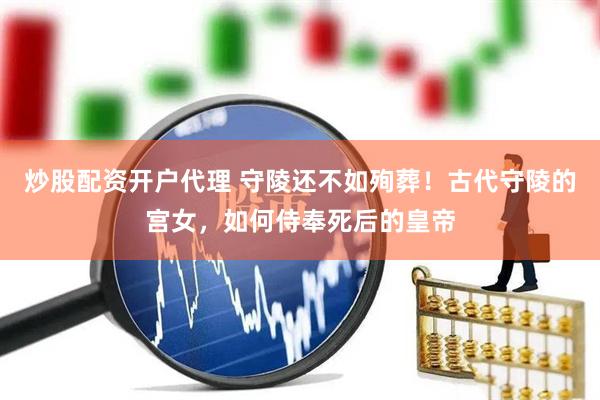我的快递又丢了配资炒股公司。
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。
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,一箱打折的抽纸,沉甸甸的,就放在门口,等着我下班回来拎进屋。
可现在,门口空空如也。
只有地面上,留下一个浅浅的、长方形的灰尘印记,像一个沉默的尸体轮廓。
空气里还残留着一点点纸箱受潮后散发出的木浆味道,很淡,几乎闻不到,但我就是知道。
我蹲下身,用手指触摸那个灰尘印记的边缘。冰凉的水泥地面,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。
走廊的声控灯应声而亮,惨白的光线泼下来,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,像个可笑的黑色感叹号。
我知道是谁干的。
是住我对门的张阿姨。
我没亲眼见过,也没有证据。但我知道。
我们这栋老楼,电梯慢得像个快断气的老人,监控更是十年前的古董,常年罢工。邻里之间,除了点头之交,几乎没什么往来。
只有张阿姨,她像这栋楼里一个游荡的幽灵,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,出现在楼道的某个角落。
她的门,总是虚掩着一条缝。
那条缝里,透出的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,还有一股子陈年旧物混合着灰尘和樟脑丸的气味。
有时候我加班回来晚了,电梯门一开,就能看到她站在自家门口,也不开灯,就那么静静地站着,像一尊风干的雕塑。
她看我的眼神,很奇怪。
不是审视,也不是好奇,而是一种……空洞的打量。仿佛在透过我,看别的什么东西。
第一次丢快递,是一小袋猫粮。我以为是快递员放错了地方,没在意。
第二次,是一本新出版的画册,外面包着厚厚的防水膜。那天下了雨,我回来的时候,只在门口看到一滩被踩得模糊的湿脚印。
第三次,就是今天这箱抽纸。
我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心里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沉甸甸的疲惫。
像一团湿透了的棉花,堵在胸口,喘不过气。
我不想去敲门质问。
我能想象到那扇门打开后,她会用怎样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,矢口否认,或者干脆沉默不语。
那样的对峙,像用拳头去砸一团棉花,毫无意义,只会让自己更难受。
我拿出手机,打开购物软件,找到了那箱抽纸的订单,点击了“再次购买”。
这一次,在支付页面,我犹豫了一下,指尖划过屏幕,点选了“货到付款”。
做完这一切,我才拧开自己家的门锁,走了进去。
屋子里的空气是清冷的,带着我离开时一整天的静止。
我没有开灯,就那么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。
窗外,城市的霓虹像一片遥远而模糊的星河,安静地闪烁着。
我想,七天,快递差不多就该到了。
到时候,一切都会有个结果。
接下来的几天,楼道里异常安静。
张阿姨那扇常年虚掩的门,也关得严严实实。
我甚至开始怀疑,是不是自己猜错了。
也许,真的只是快递被别人顺手牵羊了。这个老旧的小区,人来人往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我每天下班回家,走出电梯的第一件事,就是下意识地看一眼对面的那扇门。
那扇深红色的木门,油漆已经斑驳脱落,露出底下暗沉的木色,像一张苍老而布满皱纹的脸。
门上没有贴春联,也没有挂任何装饰物,只有一个锈迹斑驳的旧门牌号。
它就那么沉默地立在那里,把一个世界,隔绝在门后。
我开始留意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细节。
比如,每天清晨,清洁工拖地的声音会在楼道里回响,水桶和拖把碰撞的声音,哗啦啦的,带着消毒水的味道。
但那声音,总是在张阿姨的门口戛然而止。
我特意早起过一次,悄悄打开门缝看。
清洁阿姨推着车,熟练地拖着地,到了张阿姨门口,却自然而然地绕了过去,仿佛那里有一道无形的屏障。
再比如,我从未见过张阿姨家里有客人来访。
也从未听过她家里传出电视声、说话声,或者任何属于“生活”的声音。
她就像一个孤岛,漂浮在这片由钢筋水泥构成的海洋里。
我的工作是修复旧物。
古籍、字画、破损的陶瓷……那些被时间侵蚀、被世人遗忘的东西,在我手里,一点点恢复原貌。
这是一份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。
我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,对着一页残破的书卷,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揭开粘连的纸张,用特制的浆糊,把细小的碎片重新拼合。
我的工作台,总是弥漫着一股旧纸张、墨水和修复药剂混合的气味。
我喜欢这种气味。
它让我觉得安宁,仿佛能触摸到时间的脉络。
这几天,我手头正在修复一幅清代的山水画。画心被虫蛀了几个小洞,边缘也有些残损。
我戴着放大镜,用细如毫毛的笔,蘸着特调的颜料,一点点地补全画上的山石纹理。
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,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时间,在这一刻,流淌得缓慢而温柔。
可我的心,却静不下来。
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到对面那扇紧闭的门后。
她在里面做什么呢?
一个人,一整天,一整个星期,甚至更久。
她会觉得孤独吗?
还是说,她早已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?
我甚至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关于“独居老人”和“囤积癖”的新闻。
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和文字,让我感到一阵阵心悸。
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我怕自己的想象,会变成一种残忍的窥探。
第七天很快就到了。
是个周末,我没有去工作室,待在家里。
上午十点左右,我的手机响了。
是快递小哥的电话。
他的声音年轻而富有活力,带着一点点的喘息:“您好,是X先生吗?您有一个货到付款的快递,我现在在您楼下。”
“好的,我马上下来。”我回答。
“那个……先生,”他顿了顿,似乎有些为难,“这个件,我前两天来过两次,您都不在家。今天再送不到,就要被退回去了。”
我的心,咯噔一下。
“前两天?”我问。
“是啊,大前天下午来过一次,昨天上午也来过。敲您家门没人应。”
我愣住了。
大前天和昨天,我都在家。
我没有听到任何敲门声。
一个念头,像一道闪电,瞬间划过我的脑海。
“你等一下,”我的声音有些干涩,“你是不是……敲错门了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不会吧?XX栋XX单元701,没错啊。”快递小哥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。
“你再看看,是不是敲了对面的702?”
“702?”他似乎在回忆,“好像……是有个阿姨开的门。我问她是不是X先生,她说不是,说家里没人叫这个名字。”
“她跟你说什么了?”我追问。
“她就问我,这箱子是给谁的。我说是一个叫远生的。她说她不认识。”
远生。
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我的心,猛地沉了下去。
“你等我,我马上下去。”
我挂了电话,抓起钥匙就往外冲。
我几乎是跑着下楼的。
老旧的楼梯,发出“咚咚咚”的沉重回响。
我看到那个年轻的快递小哥,正蹲在楼下的花坛边上,旁边放着一个半人高的纸箱。
他看到我,站了起来,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。
“不好意思啊先生,可能是我真搞错了。”
我摆摆手,喘着气,指着那个箱子:“这是我的件。”
“啊?”他愣住了,“可是收件人写的不是……”
“是我买的,”我打断他,“地址是我的,电话也是我的。只是收件人名字,我随便填的。”
这是一个谎言。
我当时下单的时候,鬼使神差地,在收件人一栏,填了一个我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小说里的人物的名字。
远生。
我甚至不记得那本小说讲了什么,只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。
我付了钱,签了字。
快递小哥一脸“原来如此”的表情,骑着他的电动车,很快消失在小区的林荫道里。
我一个人,站在那个巨大的纸箱旁边。
阳光很好,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下细碎的光斑。
有风吹过,树叶沙沙作响。
我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
原来,她不是什么都拿。
她只是在等一个叫“远生”的人的包裹。
我费了很大的力气,才把那个箱子拖上楼。
电梯里,只有我和这个巨大的箱子。
镜面一样的电梯壁上,映出我有些狼狈的脸。
我看着自己的眼睛,里面充满了困惑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
回到七楼,我没有立刻把箱子拖回家。
而是把它,轻轻地,放在了702的门口。
然后,我退后几步,靠在自己家的门上,静静地等待着。
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。
或许,我只是想知道,当她打开门,看到这个写着“远生”名字的箱子时,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楼道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“砰、砰、砰……”
一下一下,沉重而有力。
大概过了十分钟,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久。
对面那扇深红色的门,传来了一声轻微的“咔哒”声。
门,开了一条缝。
和我之前无数次看到的一样。
一只苍老、干瘦的手,从门缝里伸了出来,搭在门框上。
那只手,皮肤像揉皱了的牛皮纸,上面布满了褐色的老年斑和暴起的青筋。
然后,我看到了张阿姨的脸。
她比我印象中要苍老得多。
头发花白,稀疏地贴在头皮上。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,像干涸的河床。
她的眼睛,浑浊得像蒙上了一层灰的玻璃珠子,此刻,正死死地盯着门口的那个箱子。
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,似乎想说什么,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她的目光,从箱子上的快递单,缓缓地,移到了我的脸上。
那一瞬间,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情绪。
不是贪婪,不是心虚,不是被抓包后的惊慌失措。
而是一种……巨大的、深不见底的悲伤。
还有一丝,微弱的,几乎要熄灭的希冀。
像寒夜里,最后一颗微弱的星。
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,对视着。
楼道的声控灯,因为长时间的静止,熄灭了。
我们都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。
我能听到她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。
“是……是远生的吗?”
她的声音,沙哑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,每一个字,都说得异常艰难。
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我只能,默默地,点了点头。
她眼里的那一点点光,瞬间就亮了起来。
那是一种,绝处逢生般的光亮。
她颤抖着,伸出另一只手,想要去触摸那个箱子。
可她的手,在半空中,停住了。
她又看向我,眼神里充满了恳求。
“我……我没有钱。”她说。
我这才想起来,这是个货到付款的件。
“没关系,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响起,有些飘忽,但很清晰,“钱,我已经付过了。”
“这是……他送给我的礼物。”
她没有问为什么,也没有怀疑。
她只是喃喃自语着,仿佛在说服自己。
她用尽全身的力气,把那个巨大的箱子,一点一点地,拖进了门里。
那个过程,漫长而艰难。
她的身体,佝偻着,像一张被拉满了的弓。
箱子的边缘,在水泥地上,划出刺耳的“沙沙”声。
最后,门,在我面前,缓缓地,关上了。
“吱呀——”一声,像是谁的一声叹息。
楼道,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我靠着门,缓缓地滑坐到地上。
冰冷的地面,透过薄薄的裤子,传来一阵寒意。
我抱着膝盖,把脸埋在臂弯里。
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。
直到双腿发麻,我才扶着墙,慢慢站起来。
我回到家,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
握着杯子的手,还在微微发抖。
窗外,太阳已经偏西,金色的余晖,给城市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边。
我的心里,却下着一场冰冷的雨。
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,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好像是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模型,很复杂,需要自己动手拼装。
我买它,只是一时兴起。
我喜欢那些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东西,它们能让我的心静下来。
可现在,它去了它更应该去的地方。
远生。
他到底是谁?
是她的儿子吗?
他去了哪里?
为什么,她会觉得,他会给她寄快递?
无数个问题,像无数只蚂蚁,在我的心里啃噬着。
那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。
我梦见自己,站在一片无垠的星空下。
那些星星,又大又亮,仿佛触手可及。
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孩,背对着我,正在调试一架巨大的天文望远望镜。
我看不清他的脸。
我只听到他对我说:“你看,那颗星,是我发现的。我给它取了个名字,叫‘母亲’。”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。
在遥远的天际,有一颗星星,散发着温柔而微弱的光芒。
它不耀眼,却让人感到无比的安心。
我醒来的时候,天还没亮。
窗外一片青灰色。
枕头,湿了一片。
从那天起,我开始有意无意地,关注起张阿姨的生活。
我会在出门的时候,悄悄在她门口放一袋新鲜的水果。
会在下雨天,把她的窗户关好。
我甚至,开始以“远生”的名义,给她买东西。
有时候是一件厚实的毛衣,有时候是一盒她可能爱吃的点心,有时候,只是一束小小的,开得正艳的雏菊。
我依然选择货到付款。
然后,在快递小哥联系我的时候,提前把钱付掉。
每一次,快递小哥都尽职尽责地,把包裹送到702的门口。
我不知道,张阿姨在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,是怎样的心情。
我只知道,她门口那条常年存在的缝隙,不见了。
门,总是关得紧紧的。
但有时候,我会在半夜听到,从她门里,传来一阵阵压抑的、低低的哭声。
那哭声,像一只受伤的小兽,在黑暗中,独自舔舐着伤口。
每一次听到,我的心,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,紧紧地揪住。
我开始向楼里的老住户打听张阿姨的事。
他们大多都摇摇头,说不太清楚。
只知道她在这里住了很多年,一直都是一个人。
只有一个住在五楼的王奶奶,她在这里住了快四十年了,她说她记得。
“你说702的张姐啊……唉,也是个可怜人。”
王奶奶坐在楼下花园的长椅上,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叹着气。
“她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她老公走得早,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,可出息了。”
“她儿子,就叫远生。那孩子,从小就聪明,爱学习。不爱说话,就喜欢看天上的星星。”
王奶奶的眼神,飘向了远处,仿佛在看一段很遥远的过去。
“后来,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学的就是天文。听说是要当科学家的。张姐那时候,天天把儿子挂在嘴边,骄傲得不得了。”
“那后来呢?”我问。
王奶奶的脸色,沉了下来。
她沉默了很久,才缓缓开口:“后来……那孩子,就没回来。”
“是……出什么事了吗?”
“听说是,大四那年,去一个很远的山里观测站实习,出了意外。雪崩,整个观测站的人,都没了。”
王奶奶的声音,越来越低。
“那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。张姐接到消息,一个人去了那边。回来的时候,整个人都变了。”
“她不说话,不见人,就把自己关在屋里。我们这些老邻居,去看她,她也不开门。”
“再后来,她就开始……有点不正常了。”
“她总说,她儿子没死。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,去看星星了。总有一天,会回来的。”
“她开始到处捡东西,人家不要的纸箱子、瓶子,她都往家里搬。她说,要给儿子留着,等他回来用。”
“再后来,她就开始等快递。她说,儿子会给她寄东西回来。每天,她就守在门口,等着快递员。”
王奶奶说到这里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“都快十年了。你说,这人啊,心里有个念想,是好是坏呢?”
我没有回答。
我只是觉得,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,喘不过气来。
那天,我和王奶奶聊了很久。
我知道了,张阿姨的丈夫,在她儿子上初中的时候,就因病去世了。
她一个人,在纺织厂上班,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。
远生是她全部的希望和寄托。
我还知道了,远生出事后,学校和相关部门给了她一笔抚恤金。
但她一分钱都没动。
她把那些钱,都存了起来。她说,那是给儿子娶媳半用的。
我回到家,坐在窗前,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
城市里的灯,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。
像一片,人间的星海。
我想象着,一个叫远生的男孩,曾经也无数次地,站在这扇窗前,仰望着真正的星海。
他的心里,装着宇宙,装着未来,装着对母亲的爱。
可这一切,都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,戛然而生。
而他的母亲,用自己的方式,为他延续着生命。
她把他,安放在一个,只有她自己能看到的世界里。
在那个世界里,他没有离开。
他只是,去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,继续追寻他的星星。
他会记得给妈妈寄礼物,会告诉她,他一切都好。
我拿起手机,又下了一单。
是一本很厚的,关于星空摄影的画册。
在收件人一栏,我认真地,一笔一划地,输入了“远生”两个字。
这一次,我没有选择货到付款。
我不想再让那个年轻的快递小哥,去面对一个母亲的悲伤和期盼。
我希望,当他把包裹送到她手上的时候,可以轻松地说一句:“阿姨,您的快递。”
而不是,小心翼翼地问:“请问,您是远生吗?”
日子,就这样,一天天过去。
我依然会以“远生”的名义,给张阿姨寄东西。
我开始研究她的喜好。
从王奶奶那里,我打听到,张阿姨年轻的时候,喜欢听评弹,喜欢吃桂花糕。
于是,我给她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,调好了评弹的频道。
我从一家老字号的糕点铺,给她订了最新鲜的桂花糕。
我甚至,还给她买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穿的,柔软舒适的鞋子。
我做这些,并不是出于同情或者怜悯。
我只是觉得,一个母亲的爱,不应该被如此残酷地尘封。
我想,如果远生还在,他一定也会这样做。
我只是,在替他,完成那些他没来得及做的事。
我不知道张阿姨有没有意识到,这些快递,其实都来自对门的邻居。
也许她知道,只是不愿意戳破。
也许她不知道,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那个美好的梦里。
这都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我发现,她开始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。
有一天,我下班回家,闻到楼道里,飘着一股淡淡的饭菜香味。
那香味,是从702的门缝里飘出来的。
虽然只是简单的青菜和米饭的味道,但那,是属于“生活”的味道。
还有一次,我听到她屋里,传来了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评弹声。
声音不大,却像一缕温暖的阳光,照进了那间常年阴暗的屋子。
我甚至有一次,看到她出门了。
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深蓝色的外套,头发梳理得很整齐。
她走得很慢,背影依然佝偻,但步伐,却比以前稳健了许多。
她没有看到我。
她只是,慢慢地,走向了电梯。
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。
也许是去楼下的小花园散步,也许是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。
但无论去哪里,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她开始,愿意走出那扇门,重新接触这个世界了。
我的工作依然很忙。
修复旧物,是一件极其耗费心神的事情。
但每当我感到疲惫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张阿姨,想起那个叫远生的男孩。
我会觉得,我所做的这一切,都充满了意义。
我修复的,不仅仅是那些残破的器物。
更是一个,破碎的灵魂。
有一天,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修复委托。
委托人,送来了一架老式的天文望远镜。
镜筒的油漆已经剥落,支架也有些松动,最重要的目镜,更是布满了划痕,几乎无法正常使用。
委托人说,这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。
他父亲,生前是一位天文爱好者。
他说,他希望我能把它修复好,让他可以,用父亲的望远镜,再看一次星空。
我接下了这个委托。
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,小心翼翼地,把望远镜的每一个零件都拆卸下来,清洗,打磨,上油。
最难修复的,是那枚目镜。
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用最传统的手工研磨方法,一点一点地,磨平了上面的划痕。
当我把修复好的望远镜,重新组装起来的时候。
我透过那枚清澈的目镜,仿佛看到了,一片璀璨的星河。
那一刻,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
一个,或许有些大胆,但我觉得,必须去做的想法。
我把修复好的望远镜,交还给了委托人。
然后,我又去买了一架,一模一样的,全新的天文望远镜。
这一次,我没有寄快递。
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夜晚,我抱着那个巨大的箱子,敲响了702的门。
“咚、咚、咚。”
心,在胸腔里,剧烈地跳动着。
过了很久,门才打开。
张阿姨站在门口,看到我,和地上的箱子,愣住了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张阿姨,”我深吸了一口气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,“这是远生,送给您的。”
她的眼睛,瞬间就红了。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“他说,他知道您也喜欢看星星。他希望您,能用这个,看到他看到的那片星空。”
我不知道,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。
它们就像是,不受控制地,从我嘴里冒了出来。
张阿姨没有怀疑。
她只是流着泪,不停地点头。
“好……好……”
那天晚上,我帮她,在阳台上,架好了那架天文望远镜。
她的阳台很小,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。
我帮她,清理出了一小块空地。
当我们把望远镜对准夜空的时候。
我们都沉默了。
城市的夜空,并没有多少星星。
只有几颗最亮的,在稀薄的云层后面,孤独地闪烁着。
还有一轮,弯弯的月亮。
“真好看。”张阿姨看着目镜,轻声说。
她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满足的喟叹。
我站在她身后,看着她瘦小的背影。
那一刻,我觉得,她离她的儿子,很近,很近。
从那以后,我开始经常去她家。
有时候,是帮她修理一下接触不良的开关。
有时候,是陪她一起,听一段评弹。
大多数时候,我们只是,坐在阳台上,一起看看天。
我们聊得不多。
她很少主动提起远生。
但我知道,他一直都在。
他在那架望远镜里,在那段评弹里,在那块桂花糕的甜糯里。
他无处不在。
她的屋子,我终于看清了全貌。
和我之前想象的,不太一样。
虽然堆满了东西,但并不脏乱。
那些捡来的纸箱、瓶子,都被她分门别类,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角落。
客厅的墙上,挂着一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。
照片上,是一个笑得非常灿烂的年轻人。
他穿着一件白衬衫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眼睛亮晶晶的,像盛满了星星。
他就是远生。
照片的旁边,是一个书架。
上面摆满了各种关于天文的书籍。
每一本,都用透明的书皮,包得好好的。
还有一个房间,门总是关着。
张阿姨从不让我进去。
她说,那是远生的房间。
要等他回来,才能打开。
我尊重她的想法。
我知道,那扇门背后,是她为儿子,保留的最后一个,完整的世界。
有一天,我正在工作室修复一卷古画。
我的手机响了。
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我接起来,电话那头,是一个焦急的女人的声音。
“您好,请问是张惠兰女士的家人吗?”
张惠兰,是张阿姨的名字。
我的心,猛地一紧。
“我是她的邻居,她怎么了?”
“她晕倒了,在菜市场。我们现在把她送到市中心医院了,您能过来一趟吗?”
我放下手里的活,立刻赶去了医院。
在急诊室的走廊里,我见到了张阿姨。
她躺在病床上,闭着眼睛,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。
医生告诉我,是突发性脑溢血,情况很危险,需要马上手术。
手术需要家属签字。
我毫不犹豫地,在“家属”那一栏,签下了我的名字。
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。
我在手术室外,来来回回地踱步。
那种感觉,比修复任何一件国宝级的文物,都要紧张。
我给王奶奶打了电话,告诉她这边的情况。
王奶奶很快就赶来了。
她带来了张阿姨的医保卡和一些证件。
我们一起,守在手术室门口。
王奶奶告诉我,张阿姨有高血压,很多年了。
但她一直不肯好好吃药。
她说,她要等儿子回来,带她去北京的大医院看。
天快亮的时候,手术室的灯,终于灭了。
医生走出来,摘下口罩,对我们说:“手术很成功,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”
我和王奶奶,都松了一口气。
张阿姨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。
因为疫情,不能探视。
我每天,都会去医院,向医生了解她的情况。
然后,再把情况,告诉楼里的老邻居们。
大家自发地,组织起来。
有的人,负责每天去医院送饭。
有的人,负责去她家里,帮忙浇花,打扫卫生。
那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,孤僻的老人,在这一刻,成了整栋楼的牵挂。
在她住院期间,我帮她,整理了一下她的家。
我打开了那扇,她一直不让我进的,远生的房间。
房间里,和我预想的,完全不同。
没有灰尘,没有杂物。
一切,都整洁得,像昨天才有人住过一样。
床上的被子,叠得方方正正。
书桌上,还放着一本摊开的,关于行星运动的书。
旁边,是一支钢笔,和一个笔记本。
仿佛主人,只是暂时离开了,很快就会回来。
整个房间,都充满了阳光的味道。
我知道,这是张阿姨,每天都会进来打扫的结果。
她用这种方式,维持着儿子“还在”的假象。
在书桌的抽屉里,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,上锁的铁盒子。
我没有钥匙。
我把它,带到了我的工作室。
我用专业的工具,很轻易地,就打开了那把小锁。
盒子里,没有我想象中的,贵重的物品。
只有一沓厚厚的信。
还有一张,已经泛黄的,火车票。
火车票的终点,是北京。
日期,是远生出事前的第三天。
信,是远生写给她的。
一共十二封。
从他上大学的第一年,到他出事前的最后一个月。
每一封信,都写得很长。
他跟她讲,北京的天气,学校的趣事,学习的烦恼,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他跟她讲,他在望远镜里,看到了土星的光环,看到了木星的条纹。
他跟她讲,他最大的梦想,就是能发现一颗,用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。
他说:“妈妈,等我毕业了,我就接您来北京。我带您去吃烤鸭,去逛故宫,去爬长城。我还要带您去天文台,让您亲眼看看,我工作的地方,看看那些美丽的星星。”
他说:“妈妈,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要太辛苦,不要舍不得花钱。等我,等我回来。”
信的最后,都有一句相同的话。
“爱您的儿子,远生。”
我一封一封地读着。
眼泪,不知不觉地,就流了下来。
我仿佛看到了,那个叫远生的男孩,坐在大学的宿舍里,在昏黄的灯光下,一笔一划地,给他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,写下这些温暖的文字。
我也仿佛看到了,张阿姨,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,一遍又一遍地,读着这些信。
这些信,是支撑她,活下去的,唯一的支柱。
在最后一封信的信封里,我还发现了一张,被折叠得很好的,化验单。
是一张,孕检报告。
上面的名字,是一个陌生的女孩。
日期,也是远生出事前的几天。
结果显示,怀孕六周。
我的心,像是被什么东西,重重地击了一下。
原来,远生,快要当爸爸了。
原来,张阿姨,也快要当奶奶了。
可这一切,都随着那场雪崩,被永远地,埋葬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天。
我把信和化验单,小心翼翼地,放回了铁盒子里。
我不知道,张阿姨知不知道这件事。
也许远生,还没来得及,告诉她这个好消息。
也许,这是他准备,在回家的时候,给她一个惊喜。
我决定,把这个秘密,永远地,埋藏起来。
对她来说,失去一个儿子,已经足够残忍了。
我不能再让她,承受失去一个未出世的孙子的痛苦。
张阿姨在医院,住了一个多月。
出院那天,我去接她。
楼里的很多邻居,都来了。
大家帮她,把东西搬上楼。
王奶奶,给她熬了鸡汤。
李大叔,帮她把家里坏了的水龙头,换了新的。
张阿姨看着我们,嘴唇哆嗦着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只是不停地流泪。
我扶着她,走进屋子。
屋子里,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窗明几净,阳光灿烂。
她走到阳台,看着那架天文望远镜,看了很久。
然后,她转过身,对我说:“小伙子,谢谢你。”
这是她第一次,这样称呼我。
她的眼神,清明而温和。
我知道,她什么都知道了。
她知道,那些快递,不是远生寄的。
她知道,是住在对门的这个年轻人,一直在用一个善意的谎言,温暖着她。
我笑了笑,说:“阿姨,不用客气。远生……他也会希望我这么做的。”
她点了点头,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但这一次,她的脸上,带着笑。
那是一种,释然的,温暖的笑。
从那以后,张阿姨的生活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她不再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。
她开始,和邻居们来往。
她会去楼下的小花园,和王奶奶她们,一起聊天,晒太阳。
她甚至,还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。
她加上了我的微信。
每天,都会给我发“早上好”的表情包。
她不再提“远生会回来”这样的话。
但她依然,会每天把远生的房间,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依然会,在天气好的夜晚,去阳台上,看看星星。
她只是,换了一种方式,来思念她的儿子。
她把他,放在了心里,最柔软,最温暖的地方。
而我,也依然会,时不时地,给她买一些东西。
但不再以“远生”的名义。
我会直接,敲开她的门,对她说:“阿姨,我买了些水果,给您送点过来。”
她会笑着,接过去,然后,非要留我下来,吃一顿便饭。
她的手艺很好。
一碗简单的西红柿鸡蛋面,都能做得,让人回味无穷。
她说,这都是以前,做给远生吃的。
那孩子,就爱吃这个。
每次说起远生,她的脸上,都会露出,那种骄傲而温柔的神情。
仿佛他,从未离开。
又是一年冬天。
今年的雪,下得特别大。
像那年一样。
我站在窗前,看着窗外,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
我的手机,响了一下。
是张阿姨发来的微信。
是一张照片。
照片里,是阳台上的那架天文望远镜。
镜筒上,落了薄薄的一层雪。
照片下面,配了一行字。
“远生,下雪了,多穿点衣服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,看了很久。
然后,我回复她:“阿姨,他会看到的。”
过了一会儿,她回复我一个字:“嗯。”
我知道,我们都明白。
有些人,虽然离开了。
但他们,会化作天上的星星,永远地,在夜空中,守护着我们。
他们,从未走远。
他们只是,换了一种方式,陪伴在我们身边。
就像那份,永远不会被签收的快递。
它承载的,不是物品本身。
而是一份,跨越了生死的,沉甸甸的爱。
贝格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